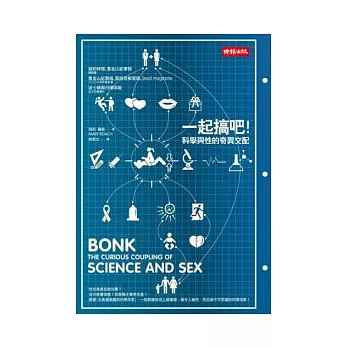Mary Roach《活見鬼﹗世上真的有阿飄?科學人的靈異世界之旅》(Spook : Science Tackles the Afterlife),貓學步譯,時報,2019
《深入最禁忌的消化道之旅》(Gulp : Adventures on the Alimentary Canal),黃靜雅譯,天下文化,2020
《打包去火星:NASA太空人瘋狂實境秀》(Packing for Mars),鍾沛君譯,貓頭鷹,2015
終於又是拖到人家不賣才寫,所以以前沒答應朋友幫網媒寫書評也是對的。
這裡讀墨還有售的只有《打包去火星》,當然讀墨用家還可於27/7前以本書跑自然歷史馬拉松。
Mary Roach其實不用多說,是信心保證,至少保證好笑。以前方某就介紹過她的《不過是具屍體﹗》和《一起搞吧﹗科學與性的奇異交配》,都是挑戰尷尬題材但非常幽默的作品。只要看過她的作品,就知道她的書就算盲著買也不會錯。無論從中學到多少,至少肯定讀得非常愉快。
(她還有兩本書,一本《不為人知的敵人》講軍事研究,方某為圖書館買了但未有空讀。另一本是《當野生動物「違法」時》是新書,方某未買。)
三本書的書名都非常直接,分別就是作者走訪科學家如何研究靈異事件、研究消化系統、和太空人生活各方面的問題。內容同樣都是爆笑連場。
相比而言,第一本《活見鬼》雖然好笑,但結局理應不會令看倌覺得超乎想像。因為畢竟以自然科學方法研究靈異事件,最後若非發現是騙局也只會是「查無實據」,否則那就不叫「超自然」了。所以本書有趣的地方,不在結果,而在於過程﹕科學家怎樣去研究這些事,歷史上又鬧出過甚麼「鬼」,科學家從中又找到哪些有趣的知識﹖
同樣相比而言,第二本《深入最禁忌的消化道之旅》理應是最「日常」的事,畢竟我們大部分人都不會撞鬼或者上太空(同樣不會經常見到屍體,而大部分人的性生活也很平淡—若非付之闕如的話),本書的內容卻是人人每天都接觸的事。由口鼻到腸胃,最後釋放出來的過程,「試問誰還未發生」﹖如果沒發生才是病吧。可是我們偏偏對消化過程有很多忌諱,排泄物帶病菌、肛門又靠近性器,被當成禁忌也算了,但就連食物也諸多禁忌(英美人不願吃內臟,對華人自然是很離奇的「不懂吃」)。就像作者所言,口水鼻涕、食糜和糞便都是體內的東西,但一流出來就變成很噁心的事。當中自然有很多故事可講。
最後一本《打包去火星》講大眾視為明星的太空人生活,內容自然更引人入勝(兼入「性」)。太空人分享生活的書,這個年頭雖仍不多,但也不會少到找不到,可是應該沒人寫得像Mary Roach那麼爆笑。畢竟書中很多題材都不是太空人自己會寫的﹕太空人如何陪著你嘔、便便滿「天」飛,NASA為了太空人生活作準備,請一批人嘗試可以多久不洗澡和「躺平」三個月,甚至坊間傳聞的「太空性愛」是甚麼一回事,這些都不是官方機構和那些太空人想討論的事。所謂太空探險「挑戰人類極限」,可不只是挑戰科技、體能和智能的極限,甚至也包括暈眩和忍臭的極限。
就算沒買到電子書,我也建議看倌找本實體書看看呀。
就電子書而言,香港讀者可在公共圖書館借到《深入最禁忌的消化道之旅》和《打包去火星》,台灣讀者可以借到《活見鬼》、《深入最禁忌的消化道之旅》和《不過是具屍體》。
實體書的話,香港公共圖書館的藏量比較懸殊﹕《深入最禁忌的消化道之旅》(30間館)、《打包去火星》(25間館)、《不為人知的敵人》(15間館)、《活見鬼》(5間館)、《一起搞吧》(只在屯門)、《不過是具屍體》(只在東涌)。
(方某人其他書評書介)
(如果閣下有興趣讀電子書,經本文連結 https://moo.im/a/14vCKQ、https://moo.im/a/135rtA 購買,本人將獲得平台回饋。當然看倌不一定要經這條連結買的。)
---
筆記,或挑骨頭﹕
《活見鬼》
#67 序「如果你在瀏覽園藝、船艇之類的書籍時發現它」
不太明白《Spook》這個原書名怎麼跟園藝船艇扯上關係。
#104 1又是你﹕造訪輪迴國度「印度邦加洛(Bangalore)」
這樣譯比大陸譯「班加羅爾」好,至少省字。
#262 「探索形上學和胚胎學的深奧混合」
我本來想這是否指本體論的 ontology 譯錯了,不過胚胎學應該是 embryology。
(為何在下會搞錯﹖因為胚胎發生學是 ontogeny,感謝英文搞得那麼複雜。)
原文應該真的在提及胚胎學,作者想問靈魂如何嵌入胚胎。
#295 2精子裡的小人「希波克拉提斯無疑是從早餐中獲得啟發,他認為卵是用來提供發育中的人類食用,卵一旦吃光了,嬰兒就孵化完成:把生命的誕生說得像是去採買雜貨一般。」
這其實也不全錯,例如蛋的卵黃本身的確是供應營養給胚胎發育用。(只是他們以為精子本身就是等待發育的胚胎,卵子本身只是供應營養,這點大錯特錯。)
#312 「科學作家齊默(Garl Zimmer)」
應為 Carl。
#334 「這段文字正描述殺死一隻受傷的大象最快的方法:從大象雙耳之間脊柱頂端敲入一根木樁。受到好奇心驅使,達文西以同樣的手法破壞了一隻青蛙的脊髓。「那青蛙在脊髓被穿過之時立刻死亡。」
術語叫 pithing,但科學實驗室用的通常是金屬棒/針,可能因為金屬更易破壞脊髓的電訊號。
#474 3如何測量靈魂的重量「卡本特(Donald Gilbert Garpenter)」
很明顯這裡的G同樣應該是C﹕ Carpenter。為何譯本會把C都當成G﹖又不是DNA。
「卡本特列出另一種利用懷孕婦女的獨特方法。在七十七頁他告訴我們:「為房子驅鬼的絕佳方法,是讓剛受精的婦女住在裡面,就在麥進入胚胎的正常時刻之前。」」
又不怕讓胎兒著魔了﹖
#490 「「每一位元的資訊損失所必須釋放的熱量,大約是3×10^-21焦耳。」納宏說。」
這不會量得到吧。就算把整個人腦的資訊加起來,可能也只算幾焦耳﹖
#508 「在天花板一角,一個螢光燈閃了一下,然後熄滅。應用熱力學第一定律,我們知道在宇宙的另一個地方,一個不漂亮但有成本效率的光才剛出現。」
幽默但非事實。(因為燈光熄滅其實不是「光消失了」,而只不過是「不繼續耗用電能變光」而已。已發出的燈光,能量並沒有消失,它要不是透出屋外,就是被牆壁和其他物品吸收變成熱而已。)
#527 「他們有一個信仰系統,讓他們『知道』答案是什麼。他們不需要可以引用的證據。而且,如果結果和他們知道的並不一致,將會是個災難。他們不想冒這個險。」
宗教界之所以反科學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對一切已有終極答案。所以任何跟這個答案不符的發現都會變成威脅。
「他參加音識科學和量子理論的聚會」
意識﹖
「史丹福直線加速器中心(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 Center)研究發展共同計畫負責人派翠克.雷(Patrick Lui)」
Lui 可以是姓雷,但也可以姓呂。
最奇的是你竟然可以在葉劉那個匯賢智庫的網站找到他,中文名叫雷柱東。
#532 「你只剩下操作系統:一種基本的、自由飄蕩的意識。」
問題是﹕沒硬件沒應用程式的操作系統還有甚麼功能﹖
#624 「宣稱不只能夠拍下生命力,而且可以用這些影像診斷疾病和情緒狀態。」
原來這種騙局在1898年就有。
#668 5難以下嚥﹕頭昏眼花的靈外質全盛期「紐約州海德司維爾(Hydesvill)」
很明顯漏了個e。
#706 「麥戈道(William McDougall)」
這個姓香港會譯成麥道高,就算要用「戈」也應該是「麥道戈」,顯然是倒轉了。
「康史塔(Daniel Comstock)」
這譯名在廣東話真是妙不可言。
#926 7笨蛋帽中的靈魂「你會覺得在這個地方,他們會砍了懷疑著,再做成午餐吃(尤其在你試過這裡的午餐之後)。」
即是午餐好不好吃﹖
#942-950 「如果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電話發明者)能夠讓一個脫離肉體的聲音穿越大陸,如果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電報發明者)可以經由空氣把無形的資訊從一個城鎮傳送到另一個城鎮,那麼創造出和「偉大上界」的連繫又會有多難呢?」
三大科幻巨擘之一克拉克有言﹕任何足夠先進的科技都跟魔法無異。
所以這個年代的人們更易相信魔術﹖
#974 8你聽得見我嗎﹖「羅迪夫雖然住在德國,但他聽到很多聲音對他說拉脫維亞語。」
分明是腦袋把雜聲空耳成自己能理解的東西。
#1001 「巴魯司不是個懷疑論者,事實上剛好相反。他告訴我他相信科學已經蒐集了可靠的證據,足以證明死後的世界以史瓦茲(見第六章)和史帝文生(見第一章)的形式存在,但他不認為電子聲音現象是其中一部分。」
正如創造論者和陰謀論者的理論經常鬼打鬼,他們唯一的共識就是不接受科學界的共識。
「但我並不意外電子聲音現象團體懷疑這項研究:如果這些聲音的來源不是靈魂,那麼是什麼?」
這其實是訴諸無知的謬誤。
#1007 「葛拉夫想起一個歇斯底里的西德女人,她的烤箱會在她開門的時候對她說話。還有一個住在附近的男人,每晚被他的暖氣系統說教。負責察看這些報告的工程師確認了,那些話是來自美國區電台的夜間放送」
廣播。日文才叫放送吧。
#1013 「在訪談了二十個這樣的病人之後,他決定同意病人的說法,這些「他者」不是幻覺,而是以不同形式存在的居民。」
醫生跟病人一起瘋。
「聽聲網酪組織」(Hearing Voices Network)」
應為「網絡」。
#1049 「坎特伯里總主教」
通常叫坎特伯里大主教。
「顯微鏡現在得和發電機鏡(Dynamoscope)和心靈傳動鏡(Telekinetoscope)分享實驗室工作台了。」
這裡 dynamo 不是指發電機吧﹖似乎是跟肌力計有關的東西。
#1084 「《發覺古董留聲機》(Discovering Antique Phonographs)」
應為「發現」。
#1102 「現在,電力、無線電波、電話技術已經是日常生活的東西了。他們離開神祕的領域」
對神秘主義者而言仍然是。
#1208 9在鬧鬼室中「「乳牛複合雜構」(Dairy Cattle Complex)」
應為「機構」。
「微特斯表(microTesla)」
應為「微特斯拉」。
#1277 10傾聽小精靈「人們認為老虎使用次聲波警告溫體入侵者,好處是可以傳送到很遠的距離,並穿透密集的樹葉。」
似乎是指溫血動物﹖但只有溫血動物聽得到次聲波﹖(但維基百科說短吻鱷也會用次聲波溝通)
#1319 11查芬和穿大衣的死者「在評審團宣示之後,法官宣布進入午餐休息時間。」
應為「陪審團」。
「強生排除了第二份遺囑造假的可能性,他的根據是,不只那些證人,連被告本身,也就是馬歇爾的遺孀蘇西,都同意第二份遺囑的筆跡是詹姆士.L.查芬的。」
我想嚴格而言她沒有被(刑事)控告,似乎不應稱被告,而應該叫抗辯人﹖
不過檢查《香港法概論》(三聯,1999版,p.62),一般民事官司和遺囑訴訟的雙方也是叫原告(plaintiff)和被告(defendant)。所以沒錯。
「來自一位心靈研究學會榮譽官員沙爾特(W. H. Salter)」
一個普通學會的officer並不是「官員」。
我想「心靈研究學會」這類組織應該沒有正式中譯,但一般學會的officer通常就是叫「幹事」或「理事」之類。所以大可譯成「榮譽幹事」。
#1353 「︽聖經︾」
這是直排的書名號(直排時能正確顯示),但電子書的出版社預設為橫排。
#1397 「無論旦是誰選擇了詹姆士.L.查芬墓碑上的題辭」
多了個「旦」字。
#1435 12六呎之上「有些人想起自己在不超過天花板的地方遊盪,像一團熱空氣一樣從自己身上浮起來。有些人記得高速穿越某種隧道,通常朝向一片光,有時朝向已逝的親友。」
這跟發夢有何分別﹖
#1447 「英國南漢普頓」
港譯修咸頓。
「拉曼爾驚訝於心臟停止瀕死經驗的醫學矛盾:意識、感知、記憶似乎依然運作,但這個期間病人失去「所有皮質和腦幹的功能……這樣的一個腦,就像是拔掉電源、拆解電路的電腦。它不能產生幻覺,什麼事也不能做」」
這想法有誤。心臟雖停頓,但腦細胞並不會立即死亡,它們還是會活動一段時間,在缺氧狀態下掙扎一會。
其實「瀕死經驗」正正是腦細胞掙扎活動的結果。
#1461 「薩崩(Michael Sabom)是第一個涉入瀕死經驗研究的心臟內科專家」
為何會把人名譯個「崩」字出來﹖譯「薩朋」不行嗎﹖
---
《深入最深忌的消化道之旅》
#336 第二章「品嘗味道卻沒有任何感知體驗,聽起來似乎難以想像,然而你現在或許正是如此。人類的腸道、喉部以及食道上端都有味覺接收器細胞,不過,只有舌頭的接受器會向大腦報告。」
有人另外問為何睪丸會有味覺受體。
#354 「大家都肖想成為咪咪樂」
是「超」吧。
#385 「這種髮型叫作赫本頭」
香港叫夏萍。
#521 第三章「獨角鯨是中型的鯨,一根長長尖尖的角從頭上突出來,彷彿是生日蛋糕上的蠟燭。」
又真係幾似。
#533 「「牛舌香」(Beef Tongue Piquant)等食譜」
他們竟然連牛舌都不吃﹖
#580 「但生殖器官在全世界應該都不會是盤中飧」
如果他們看見牛歡喜和魚春大概會嚇暈吧﹖
#589 「有些文化會吃猴子肉,但這些文化在傳統上不吃猩猩。」
說哪裡﹖非洲﹖非洲人也有吃猩猩呀。
#606 「隨手可得的佳餚」
應為「唾手可得」,香港人經常寫錯「垂手可得」,想不到國語人也會寫錯。
#633 「L半胱胺酸的另一個常見來源是羽毛。布列的理論認為這或許能解釋雞湯的醫學價值」
但有人不拔毛就煲湯﹖
#762 第五章「搞不好還提供了政府養老金和一塊地」
明明在提及當事人跟公司通信,所以這筆 pension 應該不關政府事。
「幾年後,他的一位同事想收藏那充滿傳奇的胃,用來研究並展示於博物館。聖馬丁的遺族發來一封電報:「勿來剖屍,來者必殺。」」
可見何其反感。
#772 「他太過於強調胃酸的角色,忽略了胃蛋白酶和小腸裡的胰酵素對消化的貢獻。」
那時候(大約十九世紀)應該不會知道酵素。
#813 第六章「洗衣粉根本就是裝在盒子裡的消化道。洗碗精也一樣:晚餐客人沒吃完的食物,蛋白酶和脂酶會把它們吃掉。」
洗潔精沒酵素吧﹖
#854 「我孫女鼻涕太多的時候,我太太或我自己會用嘴巴幫她吸抹乾淨,然後再吐掉。不過,別人的小孩則甭想。」
古時已有吸涕。
#862 「說到細菌殺手,在唾液面前,漱口水只能甘拜下風。」
其實也不需要殺死所有細菌,減少數目令它們不至於導致疾病就夠。
#900 「為什麼我常看到年長的中國男子在吐口水?希雷提指出,他們吐的不是唾液,而是從肺部或鼻竇咳出的痰。她補充說,他們把痰吐出來,是因為不喜歡用手帕或面紙,他們反而覺得我們用手蒐集那些東西很噁心。」
連美國人都知了,算不算「有辱國格」﹖
#956 「一九七二年電影《巴黎最後的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中,奶油扮演的歷史性角色。」
吾生也晚,不查一下不知道有甚麼角色。
#1023 第七章「喉頭(聲箱)會擋住食道入口」
擋住食道入口的應該是「會厭」吧﹖(聲箱是它下方被播住的部分)
#1044 「小朋友吸入的倘若是塑膠動物或玩具士兵反倒好一點,因為從動物的腿或士兵的槍桿縫隙還能吸入空氣。」
而且還有玩具安全標準,要求玩具設計就算被小孩放入口也不會完全堵住喉頭引致窒息。
#1157 第八章「事情的原委比較可能是動物早就躲在便盆裡或床底下,只是一直沒被發現。而這些論文的作者,要不是懶得多用點腦筋,就是狡猾的事業投機分子。」
又不能太苛刻,那時(十九世紀)科學方法也未發達吧。
#1191 第九章「十到二十秒之內,麵包蟲竟然咬破動物的胃跑出來。」
有那麼厲害的話,吃牠們的爬蟲類早就絕種吧。
#1243 「「如果胃裡面有個弱點呢?」這樣的話,麥皮蟲有沒有可能藉由某種特別強力的扭動,把胃撐破逃出來?」
那麼胃本身就會被胃酸蝕穿,不用等麥皮蟲了。
#1299 第十章「他是胃腸專科醫生兼維吉尼亞聯邦大學的醫學教授」
好像未聽過這所大學﹖上網找找原來真的有,孤陋寡聞。
#1333 「名為馬考斯基(Markowski)的外科醫生指揮官」
奇怪外科醫生有上司,但何來有指揮官﹖當然書中說的應該是軍醫。
上網查看原來英國皇家海軍有 Surgeon commander,應該就是指這職位,但其實英國政府官員的 surgeon並不見得要是「外科醫生」。雖然引例中的那位甚至是牙醫 dental surgeon,可是正如香港早年的 colony surgeon 是「殖民地醫官」,他管的也不限於外科而是所有醫務問題。大概因為早年醫官都是跟隨軍隊外派到前線,懂外科比較重要,故名。現在軍隊的 surgeon general 也是譯成軍醫總監,所以我想這個職位譯成「軍醫總監」或「醫務總監」更貼近實際。
#1375 第十一章「「體孔安全掃描器」(Body Orifice Security Scanner」
這裡 security 應是「保安」,是為了保障監獄安全,不是保障被檢查者(的體孔)安全。
#1579 第十二章「以下是為「安全農場節目」(Safe Farm Program)」
這裡 program 應是「計劃」而非一個電視節目之類的。
#1726 第十四章「二來是測試號稱可以吸附那些臭氣的用品」
這應是搞笑諾貝爾獎的研究吧。
#1862 「胃腸專科醫生瓊斯說得最好:「每個肚子不舒服的人,只要上個廁所大大解放一下,就會覺得好多了。依我看,根本不需要求助於任何東西。」」
瀉藥或灌腸劑呢﹖
「家樂是提倡粗纖維的重要人物。他主張,健康的結腸每天要清空三、四次,這是「大自然的規畫」」
多於三次現在應該會當腹瀉吧﹖
「家樂多次「專程」前往倫敦動物園,為了探討動物上廁所的習慣。家樂提到,黑猩猩「每天大便四到六次」(全都拿來丟動物園的遊客)。」
但家樂氏不是美國人麼﹖為何有美國的動物園不去要去倫敦的﹖
#1878 「追蹤了三千名荷蘭男子長達十三年,得到的結論是:「男子排便頻繁與直腸癌的風險增加相關,而便祕與風險降低相關。」」
那麼我就是高風險囉﹗不是說纖維預防大腸癌﹖
#1898 「迴盲瓣是防止液體從下方進入的安全完美的屏障」
要不然我們一早被自己的大腸桿菌殺死了吧。
#1918 註13「他提到他的實驗室兔子:「我用糞便萃取物實施靜脈注射,牠顯現出沮喪與腹瀉的症狀。」」
沒死算好運了﹖
#1966 第十五章「前美國總統賈飛德(James Garfield)」
不是直接學那隻貓叫「加菲」就好﹖(維基百科叫「加菲爾」或「加菲爾德」,多個字的顯然是大陸譯法。雖然正如那隻貓的名字,我覺得連「爾」字也是多餘。)
當然,如果以香港的英式漢譯而言,「賈飛德」亦算美譯。
「霖牛肉類肽(peptonoid)」
看中文我反而不太明白是甚麼了,看英文我反而猜到是水解蛋白產品。
#2010 「坦尚尼亞哈札族的女人也用類似的方法,蒐集狒狒糞便中軟化的猴麵包樹種籽,洗淨、曬乾後搗碎成粉」
貓屎咖啡聽得多,狒屎種籽倒沒聽過。
#2053 「對於較輕微的狀況來說,心態的轉換或許會有幫助。列維特告訴我:「當看到病人只是有一點點腹瀉,我會說:『你該慶幸自己不是便祕。』」」
謝謝。
#2146 第十六章「曾有消息指出她得的病是「結腸下方」的癌症。這很像是小時候我母親把陰道稱為「前面的下面」一樣。」
是「陰部」﹖
#2194 「她有藥物成癮的問題(猴子在背上,是成癮的隱喻)」
上網一查「monkey on the back」原來是指難纏、難以擺脫的問題。不一定指吸毒,但毒癮當然是其中一種。
#2225 「一百多年來,吞鉛粒或水銀(重達三公斤)被視為破除阻塞的好辦法。」
套黃子華「阿爺」的口吻﹕「就算通渠你也不會這樣做吧﹗」
這跟玩死自己沒分別。
#2231 註5「他「為了要找一個玻璃杯」,把十四隻手指頭伸入病人的直腸裡:六隻是他自己的,另外兩位同事各用了四隻」
玻璃杯﹖這次我懷疑的不是作者或譯者搞錯,而是懷疑病人的精神狀態。
#2258 第十七章「瑟道斯基(Mike Sadowsky)是教科書《糞便細菌》(Mike Sadowsky)的共同編輯」
這裡顯然是抄漏了英文書名。
「改變某人身體裡的細菌,居然比改變飲食更加有效。」
但飲食本身也會改變細菌群吧。
#2267 「今天你結腸裡的細菌種類,和你六個月大時的細菌種類差不了多少。人的腸微生物叢,大約有八○%是在分娩時由母親那裡傳過來的。」
那麼剖腹產又沒餵母乳的呢﹖由哪裡來﹖
#2418 誌謝「Andrea Bainbridge,美國醫學會歷史醫療詐騙暨另類療法收藏」
這裡 Collection 似乎應該譯成「藏品部」較妥。
#2647 參考書目「Pen Ts,ao Kang Mu by Li Shih-chen」
不熟威妥瑪拼音,未見到李時珍也不知道前面是《本草綱目》。
---
《打包去火星》
#51 倒數計時「你出了問題需要好幾周才能修好」
遠離地球和醫生甚至可能沒法修。
#97 1他很聰明,但是他的鳥很隨便「現在的太空人工作頭銜已經分成兩類(如果人造衛星彈頭專家算進去的話則是三類,這種人和老師、浪費公帑的參議員,及用公費大吃大喝的阿拉伯王子屬於同一類)。」
老師﹖
「飛行員太空人負責操控太空船,任務專家型太空人負責進行科學實驗以及發射衛星,這群專家包括了醫師、生物學家、工程師」
總好過直譯叫「裝載專家」。
#135 「庚也是飛行員,服役於日本空軍自衛隊。」
應為航空自衛隊。(他們不會用「軍」字)
#182 2盒子裡的生活「其中一個團隊是由四位蘇俄人所組成的,另一個團隊則是(國際)跨文化摸彩箱:一位加拿大女性、一位日本男性、一位蘇俄男性,以及出生於奧地利、擔任指揮官的卡夫。在二〇〇〇年的元旦凌晨兩點半,蘇俄團隊指揮官路克尤克把加拿大團隊成員拉琵艾推出攝影機拍攝範圍外,不顧她的反抗,兩度對她舌吻。強吻事件發生前沒多久,另外兩位蘇俄受試者則拳腳相向」
很明顯蘇聯當時早已解體,應為「俄國」和「俄國人」。
#187 「卡夫說她的友善舉動是一般俄國女性少有的,例如坐在他的大腿上、親吻他的臉頰:「她渾然不知自己傳達了錯誤的訊息。」」
連美國人也不會這樣吧。
#346 3星際瘋狂「其實我只是要拍一張更好的照片。」
看來也不用上太空才有這類問題,地面已有很多人是這樣。
「一般觀念中的自殺藥丸都是氟化物,而這樣的致死方法比缺乏氧氣供應而死還要緩慢而且驚懼,所以應該不太需要這種藥丸。」
應該是氰化物吧﹖沒聽過有人用氟化物自殺的。
#495 4你先請「我在地球上約重五十八公斤,但在體積小多了的月球上,因為那裡的重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所以我的體重就跟一隻小獵犬差不多。」
應是「跟地球上的一隻小獵犬差不多」。(如果小獵犬跟你一起上月球,牠同樣會變輕)
#519 「在一九五〇年代早期,隨著商務飛行變得可行,醫生也擔心搭機可能對心臟有害,對循環系統造成負面影響。當馬伯格醫生證明並非如此時,聯合航空還出於感激頒給他托特獎。」
結果出事的竟然是血栓。
#644 6丟上丟下「此時大腦開始混淆,並且因為某種尚未釐清的原因,大腦做出的回應就是讓你感到噁心。」
一般會說因為令原始人感官混亂最有可能就是食物中毒,所以大腦先讓你把胃裡的東西嘔出來再算。
#691 「他們先用標準抽痰管抽出模擬平均一口分量的嘔吐物(約九十毫升),接著再使用新的、改良過的大口徑模型。根據《美國急救醫學期刊》的報導,後者的抽取速度比前者快了十倍,也比較不會傷到肺部。」
為何﹖因為通常抽吸越快,氣壓差越大,應該越有可能傷及肺部才是。
#789 7 太空艙裡的屍體「在沒有太空梭的時代,NASA會付錢給蘇俄太空總署,讓他們把國際太空站的人員送回地球。」
仍然是「俄羅斯/俄國」之誤。
#857 註34本來重複了註33的內容,但現在看電子檔似乎已修正。
#928 8人類毛茸茸的一步「大家還把自己買的《生活》雜誌寄過去,要求漢姆幫他們「簽名」。霍羅曼的工作人員也很有毅力地遵命行事,把牠的小手一而再、再而三地壓在印泥上,數量多到現在有漢姆「簽名」的《生活》雜誌在拍賣網站上只有四美元的價值。(而且有可能是造假的。布瑞茲告訴我,當初因為怕漢姆會「累壞了」,工作人員「過了一段時間後,就開始用其他猩猩的手蓋章代替漢姆。」)」
所以何必拿簽名(或手印)。
#959 「史密斯森中心宣布他們計畫將漢姆的毛皮填充成標本,讓它成為國際太空名人堂「室內漢姆展」的展品之一,這個展覽當時的內容是「一張漢姆的照片」。民眾對此的反應非常激烈。檔案館裡保存了其中的一些信件:「各位:漢姆是國家英雄,不是一件東西……你也會提議要填充葛林的遺體嗎?」「黑猩猩不是甜椒鑲肉。」等等。《華盛頓郵報》的標題照例用了雙關語:「錯到這步田(填)地」」
大概是取 Field / Fill 同音。
#986 「讓太空船從月球起飛,再和人造衛星對接,已經遠遠超出黑猩猩的能力。但如果是直接把太空艙發射到月球著陸,那就完全可以由地面中心控制,就像現在遙控登陸的無人漫遊車一樣。」
如果真的這樣做,即是沒打算讓牠回來。
「周日增刊報紙《本周》的一篇文章暗示,蘇聯正在考慮讓太空人進行單程登月任務」
有那麼恐怖﹖
#1051 註51「和一般的看法相反,就算太空裝破掉或太空船失壓,太空人的血液也不會沸騰。他的身體可能會腫脹,但不會爆炸。某種程度上來說,身體就是一種血液加壓裝,讓溶解的氣體維持在液體形態。只有直接暴露在真空下的體液才會沸騰(就像NASA在一九六五年的一位穿著有縫的太空裝進入高度室的受試者所說,他在失去意識前記得的最後一件事,就是他的口水在舌頭上燒滾的感覺)。」
這的確是兒時在兒童科普書中經常看到的描述。
#1092 9下個加油站﹕三十二萬公里「高緯度極區的景色只保留了最自然的元素:土地和天空。」
「天與地」不就行了﹖
#1106 「有人告訴我,不過我不太相信:穿著太空裝(就算是假的)可以吸引很多女孩。」
也不出奇,象徵冒險和精英嘛。
#1160 「葛拉斯繼續抱怨任務控制中心「奪命連環扣」地打電話給他們」
原來他們是把「奪命連環call」變成國語字,我只聯想起周星馳的「奪命連環鎖」。
#1172-1181 「哈德菲爾德告訴我,出名的阿波羅十三號事件──在前往月球的途中爆炸,以及洛威與同伴採取的解決方案,其實已經被NASA「模擬過」至少一次。顯然洛威在太空中做的每件事,在地面都模擬過了。包括兩周不洗澡。」
雖然前面才說「做了失敗的計畫就是打算讓計畫失敗」,但預先計劃做準備還是不可或缺。畢竟就算計劃失敗還是要盡力讓乘員生還。
#1225 10休士頓,我們發霉了「這個計畫對於受試者來說這麼難受,對研究人員來說也不像玫瑰花瓣那麼浪漫。多虧了他們反覆地嗅聞,才能找出結論:「體味最重的是腋下、鼠蹊部,以及雙腳。」」
這還要做實驗才知道﹖
#1274 「根據蘇聯的研究,在五到七天沒洗澡,也沒有更換油膩衣物的情況下,皮膚會停止製造皮脂。只有當人開始換衣服或沖澡後,皮脂腺才會重新開始工作。皮膚似乎在五天份的油脂堆積狀態下是最好的。……我們的皮膚比較希望我們五天洗一次澡嗎?很難說,但那些特別愛洗手的人(醫院工作人員以及某些強迫症患者)的確比較容易出現發炎或溼疹症狀。拉爾森提出一份研究顯示,百分之二十五的護士皮膚是乾燥受損的。諷刺的是,原本護士洗手是希望能避免散布傳染性細菌,但過度洗手反而讓情況更加惡化。」
很難說,如果是在溫帶地區(尤其是不太熱的季節)還好,在熱帶亞熱帶是不太可能的,因為沒一天就會很臭了。
至於後者就是非戰之罪,畢竟醫護接觸的都是病人,本來就多菌,而且可能是惡菌,無法不洗。不想傷害皮膚大概只能戴手套。
#1292 「太空人若田光一(「光一」的日文發音很巧妙地近似於英文的一起癢,co-itchy)」
這也給你想到。
#1362 11水平的二三事「蝕骨細胞移除受損的細胞」
應為移除「骨質」。
#1368 「這裡的雞肉都是方形的,我要吃帶骨和帶肉的雞肉!不要再給我那些小方塊了。」
太空人也不會吃到有骨的雞肉吧。(所以在地面模擬太空人生活的實驗對象自然也不會有)
#1397 「也不用付電視費」
看有線電視網要付費,但看無線廣播也不用付吧。
#1499 12三隻海豚俱樂部「海耶斯剛好在脫掉他的溼衣服。他是一位海洋生物學家,博士論文是斑海豹的交配策略。」
我相信原文其實是wet suit (濕式潛水衣)﹖
#1560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無重力的效果?沒有了重力將血液往下半身拉,留在上半身的血液就比較多。胸部會比較大,傳說陰莖也會因為這種膨脹而受惠。」
明明陰莖是在下半身呀。
#1619 13萎縮的高度「不曾有人從太空飛行的緊急事故中跳傘逃脫,目前也不清楚在太空飛行的各個階段裡,要怎麼跳傘才安全。」
在那麼高空高速的環境大概不大可能成功跳傘,給他們降落傘也只是以防萬一。
#1730 14分離焦慮「在零重力之下,尿液不會從膀胱的底部開始排出,表面張力會讓尿液附著在膀胱壁上。只有當膀胱幾乎要全滿了的時候,兩側才會開始拉長,引發排尿的感覺。但到了那個時候,膀胱可能已經太滿了,導致尿道受到壓迫而關閉。」
倒是沒想到在太空中連小便的時機也成問題。
#1821 「據報,目前正在太空船上進行STS任務(41-F)的太空人已經恢復使用阿波羅型的黏著袋。在前幾次任務中,零重力馬桶所產生的糞便塵雲使得一些太空人停止進食,以減少使用馬桶的需求。」
你話塵雲幾麻煩呢。(笑)
#2021 15無法撫慰人心的食物 註90「太空梭的發射重量限制迫使艾德林只能帶「一小塊聖體」和頂針大小的酒杯,好讓他在月球上自己進行聖餐禮。」
除非自己就是神職人員,否則他也只能領預先祝聖的聖餐上月球。
#1974 「諷刺的是,如果你想減少太空人的「殘渣」,你就應該給他吃他想吃的東西:牛排。動物蛋白質和脂肪是世界上最容易消化的食物。牛排的部位愈上等,愈容易消化吸收──甚至可能完全沒有「未吸收殘渣」。」
即是雪花肥牛﹖
「(蘇聯太空總署沒有升空前給太空人吃牛排和蛋的傳統,他們拿到的是一公升的灌腸劑。)」
人道問題。(這裡寫「蘇聯」沒錯,因為這是指由蘇聯時代開始的傳統。)
(補﹕又,關於書中提供太空人吃牛排還是「老鼠肉」的建議,葉綠舒指出作者的描述有偏差。)
#1989 「英蓋芬格寫:「在目前的情況下,既然短程航行是主流,我斷言排泄物處理問題最實際的解決方法,就是找便祕的太空人。」」
OK you win
#2077 16吃你的褲子「把儲藏艙留在火星的策略是訪問蘇俄太空人時提及的。」
同樣的錯誤﹕俄國。
#2095 註98「但我們要說的是垃圾壓縮機、防彈背心、高速無線資料傳輸、植入型心臟監視器、無線動力工具、義肢、手持式吸塵器、運動內衣、太陽能板、隱形牙套、電腦控制的胰島素唧筒、消防隊員的面罩。每過一段時間,科技在地球上的應用都會往意料之外的方向去。」
原來連運動內衣都關NASA事。
#2088 「在一七八〇年代,孟格菲兄弟的熱氣球創下人類在歷史上的第一次飛行紀錄時,曾有對此不屑一顧的人問富蘭克林,他認為飛行有什麼用途?富蘭克林回答:「新生兒有什麼用呢?」」
看到這句時我首先想到的是﹕這句不是法拉第回答對電力有甚麼用的質疑嗎﹖
不過如果上網查證的話,在wikiquote 的富蘭克林頁面的確找到出處,法拉第的反而找不到。
#2095 「日本的動漫迷正在向政府請願,爭取和二次元角色合法結婚的權利。」
其實問題反而是為何要法律管﹖
一般人之間的婚姻之所以要法律管,是因為涉及實際的權利和責任。可是跟二次元角色結婚,根本不會在現實世界帶來權利和責任呀。
以這個角度看,如果法律要管你跟二次元角色的婚姻,那麼你在戰爭遊戲中殺死一個二次元角色,是否也應該當謀殺罪﹖
#2108 致謝「蘇聯太空人克里卡列夫、拉維金、羅曼年科、渥里諾夫。」
再一次的,作者訪問的太空人應該都已經是「俄國」太空人了。看到一直「蘇聯/蘇俄」到末尾,我真係開始懷疑究竟是譯者譯錯,還是作者原文故意寫成Soviet了。
「舊金山公共圖書館跨館借書部門的員工」
想不到美國的公共圖書館還會提供館際互借服務。(廣告﹕《親愛的圖書館》有講述其歷史)
不像大學圖書館可提供館際互借,香港公共圖書館只有公共圖書館內部的館際互借服務。
#2469 中英對照表「《揚子晚報》 Yangtse Evening Pos」
應為「Post」之誤。
#2535 「列寧格 Jerry Linenger」
把一個美國人譯出「列寧」兩字會不會有點搞笑﹖就算對岸也只會叫他「林恩格」呀。
#2817 「三甲基二己烯酸 3-methyl-2-hexanoic」
很明顯後面還應該有個「ac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