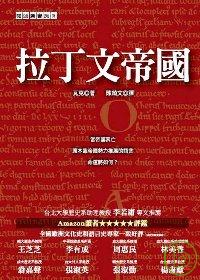(朋友找我介紹好書,於是介紹了一本2018年被另一家出版社再版,方某在2013年已介紹過的書。因為連書名也被改掉,直接放給朋友易令讀者誤解,乾脆抄一次。)
(原先由博雅出版社於2013年以《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出版)
---
繼《正義》和《錢買不到的東西》後繼續讀下去。這次聚焦在另一主題﹕以科技改造人類。
因為這本是為圖書館買的,寫不到筆記,所以唯有簡單就整體討論一下。(說簡單仍寫得那麼長,老師說話真的不可信,尤其當他說自己「講少少野」的時候。)
本書主題為是否接受基因改良,作者把「基因改良」和「基因治療」劃了界線。恢復健康的人原有的功能為治療,作者並不認為這點有問題(他在結語反駁了反對複製胚胎研究的論點,見註),但對健康的人或胚胎作基因改造,選取「更佳」基因,則為作者所不取。
作者的切入點為運動員,大概是因為這一門職業運用科技改進表現的爭議最多,最易討論。作者認為運動不只是依規則論輸贏,還是鼓勵運動員發揮天賦的才能和後天努力的鍛煉。
所以,應該接受哪些運動科技、不接受哪些,作者認為要看這種科技究竟是是突顯了「最佳選手的天份和技能」,還是扭曲了這些天份和技能,進而扭曲了一場比賽的本質。作者不贊成基因改造或其他藥物,就是因為認為這樣貶低了選手的努力,令比賽變成純表演,觀眾讚賞背後出手的科學家和藥廠,多於讚嘆選手的才華。而跑鞋或球拍就沒有這種問題。
當然這個觀點並非無可置疑,作者在《正義》就已經提及(本書中進一步解釋),有法官反對比賽本身有目的,只視為依照某些規則所作的消遣活動。而作者則不接受這種「運動消遣論」,認為沒有一個運動迷會接受這種「賽事規則只是專制,不為彰顯某些才能和美德」的結論。
對於基因改造的爭論,主要都是針對胎兒而言。作者認為「自由論」並不適用,因為胎兒本來就沒任何選擇自由可言,無論有沒有基因科技都是一樣的。「公平論」亦未必適合,因為理論上政府可以資助所有父母選擇基因,亦可以向使用基因改造的人徵稅,給沒有改造的人彌補損失。問題只是我們想不想活在這樣無止境操控競爭 的世界裡。
作者引用神學家威廉.梅(William F. May,不是維基百科上一字之差的 William E. May,神奇在兩位都搞神學的)「對不速之客的寬大」的說法,認為為人父母就是要學會約束掌控的衝動,欣賞生命本身就是恩賜。對孩子接納的愛和轉化(即栽培)的愛,要有所平衡。只懂接納就是縱容、只懂轉化又變成糾纏,把孩子當成自己的附屬物。雖然想法源自神學家,但作者認為這個想法並不依賴於宗教或神祉,對無宗教人士一樣適用。
作者認為,競爭著改變天性以適應世界,只會分散我們思考世界的注意力、和改進社會的衝勁(譯文用的是衝動)。與其用基因科技去改造人性,倒不如搞好社會和政治制度來適應不完美的人性。
---
就算看倌對生物科技完全沒興趣,這本書其實對我們來說也應該很有趣,只要看倌不理科技細節(反正書中沒有),把本書當成是美國版「千奇百趣」去讀就成。
我們很喜歡互傳那些港爸港媽如何操控他們那些寶貝港孩導致的笑話,但我想明眼人都應該知道,這種心態其實不限於「港」,華人以至東亞各族都是這樣(反而東南亞那些土著民族沒那麼重視競爭,於是南洋華人說他們 「懶」)。不過在本書中,我們見到連美國也是這樣了,父母在運動場邊么喝不特止(香港比較少這個,因為大家忽視體育),家長更打電話去大學辦公室投訴、要求行政部門向「貴子女」提供晨喚服務(好辛苦地避免用叫床)之類……洋人對「虎媽」趨之若鶩(或嗤之以鼻),但對於華人這種操練根本不以為奇吧。所以我們會說這種惡性競爭是華人「教壞」洋人的。可是,找「人生教練」去「指導人生」,不也是洋人自己發明的麼﹖
可見問題根本不在於華人或洋人,這種惡性競爭的潛力其實在人的本性之中。只是前幾百年西方資源比較充裕,令教育系統的競爭有機會放緩罷了。而東方社會則從來擺脫不了。
要再進一步,我們甚至可以說是世代之爭。因為無論是香港還是美國,「怪獸家長」(或虎媽)現象,其實都是發生在戰後嬰兒潮下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第二代人」(呂大樂說法),他們成長後生了子女,就透過種種手法(包括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有其必要,但有些措施其實在加劇跨代貧窮)去延續自己的操控。
從這角度看,所謂基因之爭其實只是表面技術問題,真正的社會問題是一批工業社會下成長和掌權的嬰兒潮世代,打算在後工業社會中繼續加強舊手法延續影響力而造成的。呂大樂口中的「第一代人」若然不是農民或難民,也鮮有像「第二代人」般在經濟發展中享盡一切優勢和機會的。戰後的社會發展開拓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空間,到現在雖非「後無來者」但也肯定不再有那麼快那麼多。
換言之,「第三、四代人」面對的是工業社會已轉型為後工業社會(資訊社會),經濟發展亦已到頂峰不再有大幅進展和大量新空間。而在「第二代人」定下的規則下,他們就是要競逐這些比以往少得多的機會,然後「第二代人」還要以己度人、嬉笑怒罵說他們不夠勤力、不夠聽話。
無論是拼命補習(東方)還是運動訓練(西方),抑或基因改造,都只不過是第二代人自認為「為小孩好」、「贏在起跑線」而做的不同操控方案而已。
分別只是東方人(如華人)早已習慣操控子女、把子女當成自己附屬品,所以不覺奇怪。而西方人有較長的獨立傳統,所以現在覺得狀況很嚴重而已。
基因改造帶來的科技問題,總有科技解決的方案。社會世代之爭的問題,則沒有解決方案。
---
回到生物科技,讀生物化學出身的在下,通常讀到這些討論都很難滿意的,因為往往覺得他們其實不太了解基因科技和遺傳學。(情況就像綠色和平的反基因改造宣傳,總令我覺得是譁眾取寵。)
就如本書,如果以為基因改良可以讓父母像訂造傢具般選擇孩子的特性、和決定他們的未來,似乎是過於「樂觀」(或悲觀,視乎你想不想這種事發生)的想法,看起來像是某些「不肖」生物科技公司欺騙父母上釣的廣告伎倆。
因為,人的性狀(即特質)絕大部分都不是單一基因控制,而不同基因之間的互相影響多到不得了,就算科學家統統研究清楚了,也不見得可以輕易操控單一性狀而不影響其他。
相對於智商或音樂才華,我想身高還是比較容易控制的,雖然也是多基因控制,但至少我們知道生長激素影響身高,那麼如果自動分泌多一點,長高的機會就大一點。可是,生長激素增加是否只有「長高」的效果﹖它一樣會帶來一堆潛在副作用。如果父母知道高生長激素除了令兒子長高一點、加入體育隊的機會增加,還會增加一些嚴重疾病的機會、甚至短命,還會覺得衡量輕重後在胎兒身上「設定」高生長素激是值得冒的險麼﹖我想有此打算的父母會少了一截。
其實基因調控大多也是這樣,是互相影響很難只有單一結果。如果要把「製造嬰兒」當成基因工程般操控(而科技上又做得到的話),你身為「設計師」也要面對坦克車設計史中「攻擊力—防護力—機動力」三者只能取其二的矛盾。到最後,要避免太偏頗產生負面效果,你的選擇可能只能均衡一點,而這樣又跟一般水平可能相差不太遠,花了大錢只能產生少許的優勢。
對於人類演化有認識的看倌,應該知道人類也是不停在演化中,而其中一個方式就是異性選擇。在沒有任何遺傳學知識的年代,人類就已經在選擇更高大、更性感、更聰明的配偶。
所以科學家面對基因改造的反對者,很多時候會感到不解。因為人類一直就在做基因選擇,只是不自覺而已。基因改造的能力當然比傳統育種手段深入、高超、快捷得多,但本質上都是在操弄遺傳物質,只是程度之別而已。
所以,就算我們擔憂基因改造孩子在倫理上的影響,那也是「程度」的問題而不是「黑與白」的問題,我們沒法在科技進展上簡單劃一條線說「到此止步」。
科學家不明白民眾的憂慮,固然不妙。民眾不明白科技「想太多了」,其實也是不美麗的誤會。
---
更有甚者,就算給你選擇到想要的性狀,也不代表孩子就會走那條路。
有很多性狀的遺傳都被研究過,最常用的是雙生兒比較,以同卵雙胞胎、異卵雙胞胎、非雙胞胎,共同生活和分別領養下出現同一性狀的機會,推論這種性狀跟遺傳有多大關係。人們研究得較多的性狀自然是「遺傳病」,當中除了一些原因很單純的,多數的病(包括糖尿病)都是有後天因素同時作用導致。
同樣地,很多其他性狀也是有後天的影響。更不要說,出現了這個性狀,不代表孩子就用得著。
以自己為例,方某相對於父母來說,算長得相當高。雖然我想這是因為營養改善多於因為碰巧拿到「高基因」,不過就算長了,也因為自小體弱多病,從來對體育運動毫無興趣。方某長大後仍是「文弱書生」,身高並沒有變成運動上的優勢。
同樣地,老媽經常說方某手指長得長又美,是彈琴的好材料,只恨當年貧窮沒錢給我學琴云云。可是,不那麼貴、人人都要學的牧童笛,方某也是肌肉協調不成,老是吹不好(雖然不知是否手指太長吹笛反而不好,因為屈得很辛苦才按到洞)。就算有錢學琴,手指協調不好恐怕也不能變成李雲迪的。
當然,要反駁的話,只是因為方某並沒有「選」到一整套合適的基因。如果手指又長、音感又好、肌肉又協調,說不定就可以成為鋼琴大師呢﹖
可是,這也不代表在下就會對鋼琴有興趣呀﹗誰知道會不會因為老媽期望甚殷,每天迫我學琴,所以自小固執的在下,反而更討厭鋼琴呢﹖(反正香港很多孩子就是這樣,幸好方媽媽沒怎樣干涉我的嗜好。)
你可以千方百計給孩子鋪一條「你認為」最好的路,但最後他可能完全沒興趣,甚至怪你為了「你要的」這些性狀而犧牲了他「本來」想要的另一些性狀,亦未可知。
以為自己可以操弄一切的嬰兒潮父母,除了要學基因科技,恐怕更該學的是混沌理論和不確定原理。先體會一下「世事難料」的道理。
---
要令這些父母三思,我想作者在書中提出的另一個理由可能更有用。
超人的箴言是「能力越大,責任越大」。作者提出的則是「控制越多,責任越大」。
如果父母對子女性狀無從選擇,那麼孩子有缺失就只是「天意如此」(當然其實有些父母也會怪自己,仍然有子女會怪「你生成我這樣」,但作者的重點是「至少可以把責任推給上天」)。但如果父母對子女的選擇和控制越多,那麼對他的人生負責則越多,真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當他們以為自己可以把子女潛在的榮耀攬上身的時候,可能沒意會到自己同時把子女潛在的失敗攬上身。因為子女的一切都受父母控制了,所以子女面臨的任何問題和失敗,自然也可以(應該﹖)歸咎於父母「選擇不周」。現在所謂的「港孩現象」,可以說是「怪獸家長」應得的報應。
我懷疑有幾多個「怪獸父母」真的意會到攬上這樣的責任有多恐怖。
(正如無知少女有需要看黃子華﹕「BB既學名﹕大肚劇痛、家嘈屋閉、賴屎賴尿、供書教學、無風無浪起碼都洗你四百萬,重係一定唔還錢﹗」)
或者,規定基因改造診所必須向光顧的父母念這一段聲明更有用吧﹕
「顧客必須留意,基因改造有其風險。就算基因改造手術完全成功和無誤,基於基因之間和基因與環境的複雜互動,可能產生不可預知的副作用,導致 貴子女面對嚴重疾病和人生失敗。
另一方面,正如基金價格,特定性狀的「市場價值」可升可跌,甚至可能變得毫無價值。(例如你為子女選擇肌肉強壯的基因,但下一代可能完全對運動沒興趣,結果只能當地盤工人。選擇音感基因,但可能再沒有人聽演奏。選擇高智商基因,但子女可能遇上另一場文化大革命。)
而 貴子弟亦可能完全不想要這些性狀,閣下在簽署本聲明時已確認放棄一切因此要求「退貨」、追究和索償的權利。
最後但同樣重要(last but not least)的是,顧客選擇了這些性狀,在道德上等於要為這些選定性狀對 貴子女造成的一切後果負責,可能包括但不限於因為「你選擇了不適合我的性狀」而被子女埋怨和怨恨一世。本公司或本國政府並不承擔因此產生終身痛苦、人身傷亡或財物損失的任何責任。
本公司代表已向閣下清晰讀出此一聲明,閣下如果仍然同意進行基因改造手術,請在下方簽名確認放棄對本公司的一切索償權利,因為手術失誤而產生的損害除外。」
這似乎是一篇科幻小說的好開頭。
---
註﹕作者反駁反對複製胚胎研究的論點,主要是連鎖推理悖論,「胚胎有成為人的潛能、和真實的人之間沒有明確界線」並不能成為「胚胎跟人沒有分別」的理由。作者舉例說假如一場火災危及一個五歲女孩和一盤二十個冷凍胚胎,所有人都會選擇先救一個女孩而不是二十個胚胎。
胚胎不完全是人類,也不純粹是物品,不是「完整的人」並不代表不用尊重(於是可以隨便利用—作者強調就算純粹是物品也不代表可以隨便糟蹋,例如在大樹或古蹟 上刻字令人厭惡,就是因為我們欣賞這些物品)。胚胎是處於「非人」到「人」之間,容許如何利用胚胎,也應該是在兩者之間。
再者,反對者的邏輯並不前後一致,例如小布殊只反對政府資助複製幹細胞研究,但如果傷害複製胚胎等於殺人,那麼就應該是禁止而非止於「不資助」,但他們卻連倡議都沒有,也沒有禁止生育診所製造數目過多、等待銷毀的胚胎。